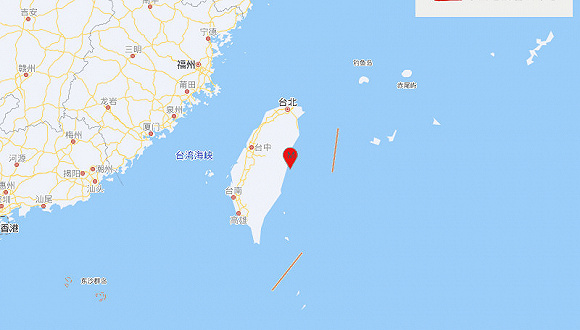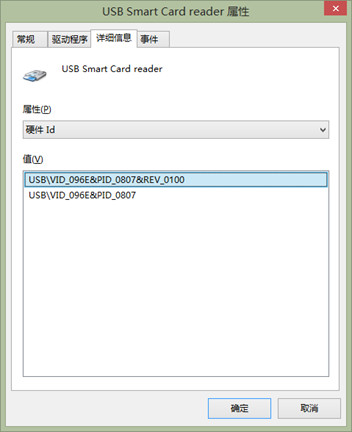阅读是一种修炼
高维生
形象的心灵性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美学》,这本书太厚了,读起来不方便,书中的插图,让我读到了另一些东西。黑格尔说:“这个世界的内容就是美的东西,而真正美的东西,就是具有具体形象的心灵性的东西,就是理想,说得理确切一点,就是绝对心灵,也就是真实的本身。这种为着关照和感受而用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神圣真实的世界就是整个艺术世界的中心,就是独立自由的神圣形象,这种形象完全掌握了形式与材料的外在因素,把它们做显现自己的手段。”黑格尔所说的真实,有很多人误解了。认为记录生活,这就是真实的,不带一点虚假。要是文字写出来的就是文学作品,那么文学不值钱了,不可能存在经典和大师。流水账的生活记录,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忽略了“绝对心灵”这是支撑文学的骨架,是灵魂。文字写出来的不都是文学,它可能是制造出来的垃圾,需要送进垃圾处理厂。
窗外新开业的商家,一首首地播放流行歌曲,在夜空中到处乱窜。我躲在书堆中在读黑格尔的书,那些音符撞在大师的文字上,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纷纷跌落,被烧得粉身碎骨。
爱和心灵的成长
美国的约翰·缪尔是我喜爱的自然主义作家,他被称为“大自然的推销者”,“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圣人”。他在美国山区生活几十年,大自然中跋涉,写下几十部关于人与自然的书。几年以前,读他的一些作品,写过有关他的文字。
这几天读《我的青少年生活》,约翰·缪尔的写了少年时代的生活,生命和一年四季的变化一样,自由和快乐地生长。他提出一个大问题,爱和心灵的健康成长。我们今天的孩子经受不起风雨的考验,大自然对于他们是符号,是电脑上的影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是春天唱着歌,走向公园,花钱认领几棵树,挂上自己的名牌。这种人有太多的功利思想,掺杂一种虚荣心,不是心灵驱使,而是对灵魂的伤害。精神背景的构筑,需要的不仅是时间,而且是真实和无私。约翰·缪尔说道:“对男孩子来说,农场生活是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把动物当成同等的生物来了解,学会尊重它们,爱它们,甚至赢得它们的爱。因此,神圣的同情心得以成长壮大,远远地超出了教堂和学校的教育。教堂和学校的教条往往是低劣、盲目、没有爱的,它宣称动物没有思想和灵魂,有获得我们尊重的权利,它们是为人类而生的,是可以让人宠爱、娇惯、屠杀或者奴役的。”想起我的少年生活,在收割后的豆地中寻找老鼠洞,发现后拢一堆豆叶,点燃后往洞里灌烟熏。逮住蜻蜓后,揪下尾巴,插上一根狗尾草,然后放飞它。这些恶作剧,带给少年时很多的快乐,当我们今天重新反思人与自然,觉得自己犯下的错误,对无知的少年时代,有一些内疚。
对待大自然,不能虚情假意,需要真心实意,要不会遭受报复的。我们今天的孩子不应是电子玩物的俘虏,而应更多的走进大自然,经受大地野性的洗礼,呼吸草的清香,与动物们称作朋友。让真实的情感,回归到生命中。
文化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读人文地理学家唐晓峰的第二本书,唐晓峰的书是将蓝推荐的,从此我关注他新书的动向。
《文化地理学释义》是他在大学课堂上的讲义,整理出的一本书。从中我学到一些东西。我们对文化是大概念,对于多层次不清楚。人们每时每刻地张开嘴就谈文化,但真正懂得文化的人有几个呢?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唐晓峰说道:“文化离不开人的思想、感情。对于单纯的客观世界,没有这个特定的文化主体,很难进行文化解释,说不出好还是坏,说不出属性,说不出价值。”他指出人在地理中的重要性,没有人的出现,地理不可能谈文化。
2012年9月,我去敦化实地考察东牟山,这座山远远地看去,平常不过了,不是奇峰险峻,更不是旅游的符号。因为在历史上,有了大柞荣建立的“震国”,有了他的影迹,使山深藏不一般的意义。一块石头,一段废弃的城墙,构成的不是想象的空间,而是真实的存在。
阅读每一本书时,书中的文字,将阅读者的记忆、经历、寻找,形成一个特殊的空间,发生文化的化学反应。
他用纯净的冰制的琴演奏
天气阴沉,天气预报说,晚上有一场雨降临。下午小睡,醒来后,读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原始森林正在消失的它们》。这本书是写他在长白山十几年的观察记录。一个人在生命最丰富的季节,躲开尘世的诱惑,教徒般地钻在一座神秘的大山中,去接近自然,将生命融合进去。这不是行为艺术,不是为了新闻做秀,某种奖项评选,而是一种召唤,这是神性的呼唤。胡冬林说:“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坚定的立场,山岩一般的宣言,表达作家的人生态度,精神的定向。中国的自然主义作家太少了,很多人关注自然时,更多的是羼杂功利的思想,他们是观光客,带着小资的情感,来享受一番,一朵野花,一条河水,一座野性的山,引起的只是新鲜的兴奋。回到水泥的城市中,听着流行歌曲,在电脑上敲下一行行的文字,码出一篇文章,炫耀地兜售自己廉价的情感。大自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休闲的地方,无尽的索取和破坏。
我跟着胡冬林的文字,循着他的情感,一起追寻青羊,使我洗净尘世的杂念,这样的文字经过大自然的养育,不会被时间所湮没掉。在伟大的自然中,不存在复制的抄袭,不是在书案上做文本实验。大自然是最好的文体,有学不尽的东西,使人变得真实,消除虚假的仿制,而是多了爱和博大的胸怀。
学者程虹翻译的“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译丛”是我喜爱的一套书。几年前读她译的约翰·巴勒斯《醒来的森林》,这几天又读她的《寻归荒野》。她在自序中说:“‘寻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走向自然,更不是回到原始自然的状态,而是去寻求自然的造化,让心灵归属于一种像群山、大地、沙漠那般沉静而拥有定力的状态。在浮躁不安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能够从自然界中找回这种定力。”她的回归和寻找,和胡冬林的寻找,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中国的自然主义作家少得可怜,生命被功利俘虏,只能空喊口号,掩盖贫血的苍白。
我还要在《狐狸的微笑——原始森林正在消失的它们》中,在长白山里行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旅行。
8点多钟,刚翻开《狐狸的微笑——原始森林正在消失的它们》,手机响起,昨天约好修太阳能的师傅上门来了。
忙乎一个多小时,换了一根送水管,打消阅读的心情。重新进入书中的情境,是另一番天地。胡冬林写在林业观测站的日子,夜晚听窗外的声音,这是一种享受,不是任何人能体验到的。“我渐渐地养成一个习惯,晚上头一挨上枕头,便静听窗外的水声。细浪一拨接一拨地款款而来,轮番舔舐岸边的沙石,发出沙沙的低吟浅唱。我觉得这是上苍赐给我的摇篮曲,每逢听到这种水声,我都会睡上一个好觉。”,我阅读文字时的窗外,一场雨洗净城市空气中的灰尘,沿街的商家不断地播放流行歌曲,不同的嘈音,好似一队队野蛮入侵的士兵,占领我的耳道,攻占心中的安静地。这时长白山区林间的恬静,对于我是敬畏的地方,变成一块圣地。阅读和现实纠缠一起,使我了一种绝望。胡冬林听着窗外,“有人在轻轻地演奏一架用最纯净的冰制的冰琴”,非虚构写作的独特感受,不听过这样声音的人,不会有感受。它使人忘掉尘世的事情撕扯,心灵静下来,情感回到生命的本源里。
阅读是一种痛苦,它使自己对身边的事物,有了清醒的认识,孤独中产生一个个为什么的疑问。
精神的火焰还在燃烧
张炜的新版《心仪》,是一本“心仪”的书。
我有一本旧版的《心仪》,扉页上有张炜先生的签名。两本不同版本的书摆在案头,时间流去十几年了,但书中的文字还是清新,精神的火焰还在燃烧。1996年11月,有一天张炜的新书《心仪》,在致远书店签名售书。我和友人坐着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穿越济南的市区。我怀念那个日子,济大路的致远书店,是一家高品位的书店,窄小的楼梯边的墙上,挂着雨果、托尔斯泰、海明威、福克纳,一些文学大师的肖像。我经过时投去热爱的目光,空间挤满书架,地中间的大案子上,摞着一层层的书。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得到张炜《心仪》的签名书。
在当代作家中,张炜是我喜爱的作家,他朴素的文字中透露诗意,这种诗意是精神的本质,如同老窖中的陈年酒,年头越久香气越足。我初读这本书是三十多岁,带着新奇、渴望,而今年过五十,重新读《心仪》,感觉不同了,对书中的文字和每一位大师的感受,发生不一样的看法,这不是年龄的问题,是思考的东西发生变化了。很多书出版的快,消失的也快,有的书是一座冰山,耸立时间的深处,让人敬仰、敬爱和向往。张炜在写卡夫卡时指出:“其实在卡夫卡这儿,是否是‘大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完全无视‘大师’们的传统。这真是少见的一类生命的感悟,那么新奇又那淳朴——我们常常发现新奇的东西往往不是那么淳朴的,所以有时那些独特性是要大打折扣的。而卡夫卡能够真实地生活在他的想象中,想象激动了他也指导了他。他在想象中获得和吸取了现实世界中绝无仅有的一份健康。” 张炜所说的真实和想象,是支撑文学的龙骨支架,离开它们,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现在的作家太缺少这两种东西,人们热衷于编造远离生活的真实和苍白的想象,作品中掺假的现象,充斥文坛。
我翻动书页,如同走进一座原始森林,书中的文学大师们的肖像,是一株株参天大树,散发一种性格和朴实的精神。
读一本好书,就是读到一个人的心灵。
我读出另一种东西
酷热说来就来,一夜过去后,热风席卷城市。厚重的水泥墙壁,挡住推进的热气,躲在房间里,读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
九十年代初,《人与事》是我着迷的一本书。记得为了买这本书,跑遍济南大小的书店。有一天上午,我和高淳海去山东大学老校散步,在路边的学生书店中,发现仅有的两本。我没有犹豫地买下,一本送给长春的傅百龄老师,他是俄罗斯文学的崇拜者,另一本我自己留下。
新版的《人与事》,换了出版社,也换了版式。打开书,看到十几幅帕斯捷尔纳克的照片,第一次走进他的影像中。这些生命中留下的影像,铺成诗人的一生,成为珍贵的史迹。它们连续流动的画面,构成人与历史的关系。童年时帕斯捷尔纳克和父母在院子里的情景,是我最喜爱的一幅,不大的院子中,父母各自坐在椅子中,手中捧着自己心爱的书在读,还没有经历沧桑的帕斯捷尔纳克,蹲在地上独自玩耍。父母间有一张空椅子,本来是他的座位。身后的房子上爬满绿色植物的藤蔓,只是进出的门口,形成拱形的空洞。画面构图讲究,摄影家用敏锐的艺术眼光,捕捉到温馨、安静的瞬间。
照片是三角形的画面,父母在一条平行线上,而儿子在他们的对立面上,而且前面是一扇房子的大门。帕斯捷尔纳克是在三角形的尖上,父母和大地托举他上升。影中深藏的暗示,不是一般人能破解得了。2013年5月11日,下午的阳光热辣,我沉在老照片中,回味帕斯捷尔纳克童年的情景。
那是普通的夜晚,但发生的事情影响一生。沉睡中的帕斯捷尔纳克,不知是被什么东西弄醒,在痛苦中哭起来。他的哭声抵不过隔壁的音乐,很快被湮没了,当“三重奏演奏”完的时候,哭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母亲来了,俯下身子亲吻他的额头,安慰惊吓中的儿子。帕斯捷尔纳克回忆,是母亲将他抱到客厅里,去见一些陌生的客人。在烛光中,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构成诗意的浪漫。这是伟大的时刻,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有两三位老人的白发和团团的烟雾混在一起。其中一位,我后来跟他很熟,而且经常见面。他是画家尼·尼·格。另一位老人的形象伴随我一生,如同伴随大多数人一样,特别是因为我父亲为他的作品画过插图,到他家去做过客,衷心敬仰他。以至于我们全家上下渗透了他的精神。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是第一次见到托尔泰的情景,帕斯捷尔纳克回忆中,对那个特殊的夜晚,充满怀念和回味。这样的场景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它如同种子,扎在人的心灵深处,一年年地长大。每一个字中,透出对大师的敬爱之情。帕斯捷尔纳克选择“渗透”,道出内心中的记忆幸福,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他无数次回到那个夜晚,是他创作的源头和出发地。
另一个影响帕斯捷尔纳克的是诗人里尔克,这两位世界级的大师,是建筑上的拱骨,支撑帕斯捷尔纳克文学的生命。
1900年,里尔克到过雅斯纳亚·波良纳,拜访过托尔斯泰。诗人认识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有书信来往,并赠送早期的诗集,写下亲切的题词。那年冬天,有两本诗集传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手中,震惊中,他阅读里尔克的诗。1959年2月4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致欧库里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变他的曲调而已,对于他的世界我无所补溢,而且我总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写出这封信时,帕斯捷尔纳克已于1958年,因为《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已经登上文学的高峰,但对于影响一生的诗人,曾经的“情敌”充满敬意,这不仅是人的品质,而是拥有一颗高贵的灵魂。美学家潘知常指出:“写作的权利意味着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而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所赢得的,正是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尊严说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很多人的写作没有底线,更谈不上尊严。情感有道德,文字也有道德,如果抛开底线去做,什么都不要谈了。年轻时读帕斯捷尔纳克,被他的诗情打动,佩服他对体制抵抗的勇气,认为这是真正的作家。多少年后,我读出另一种东西,就是他的大爱。一个社会失去爱的准则,缺少人与人之间的黏合剂,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
离开《人与事》很多年了,重读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年轻时读的是激情,中年以后读的是真实和爱。
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简朴,没有过多的华丽装饰,书橱里的一排排书,宽大的工作台,不知有多少文字是在这上面创造出来的。合上书,在和帕斯捷尔纳克作告别,书中的人与事,已经在我的心灵上扎根。